四岁那年被送走的弟弟,成了全家最硬的靠山
讲述人:张文情
第一章:寒冬降生
腊月里的风像刀子似的,刮得人脸生疼。
我蹲在灶台边上,看着铁锅里的玉米糊冒着泡,咕嘟咕嘟地响。
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,映得我的脸发烫。
里屋传来娘一声接一声的叫唤,"是个带把儿的!"接生婆突然喊了一嗓子,声音尖得能戳破窗户纸。
我看见奶奶两只手在围裙上使劲搓着,像是要搓掉一层皮似的,急急忙忙往门外走。
大伯娘站在墙角,拿袖子不停地擦眼睛,袖口都湿了一片。
外头的雪下得更大了,风卷着雪粒子往屋里钻。
我听见房檐下的冰溜子"咔嚓"一声断了,掉在院子里摔得粉碎。
小阳满月那天,大伯踩着厚厚的雪来了。
他身上的军大衣旧得发白,袖口磨得毛了边,可给我带的饼干盒却是崭新的,上头印着嫦娥奔月的画儿,嫦娥的衣带飘飘的,像是真要飞起来似的。
我把饼干盒抱在怀里,闻着那股香甜的味道,躲在门后头不敢出声。
"娃跟我们走,能念实验小学。"
大伯的声音低低的,像是怕惊醒了什么。
我看见娘坐在炕沿上,怀里抱着小阳,手指头攥得发白。
她把脸埋在小阳的襁褓里,肩膀一抖一抖的,就是不说话。
外头的风呜呜地吹,把窗户纸吹得哗啦哗啦响。
娘把小阳搂得那样紧,好像一松手,这孩子就会像灶膛里的火星子似的,"噗"的一下就没了。
炕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,照得娘的脸上一道亮一道暗的。
小阳在襁褓里动了动,发出小猫似的哼唧声,娘赶紧轻轻拍着他,眼泪却掉得更凶了。
院子里,老槐树的枯枝在风里摇晃,影子投在窗户纸上,像极了娘颤抖的手。

第二章:两处牵挂
小阳到了四岁上,还整天拱在娘怀里吃奶。
娘瘦得跟麻秆似的,前胸贴后背,可奶水却一直没断。
村里人都说,这娃是来讨债的,要把娘的骨髓都吸干了才罢休。
大伯娘每次来送奶粉,都带着城里才有的稀罕物——有时是一包动物饼干,有时是印着红双喜的奶糖。
小阳见了就扑上去,可吃完糖,又像只小狼崽子似的钻回娘怀里,两只小手死死揪着娘的衣襟,生怕被人抢了去。
大伯娘站在一旁搓着手笑,可那笑容还没到眼底就散了。
记得是收完秋粮的时候,村口突然传来"突突"的响声。
我和一群光脚孩子跑去看,只见大伯开着辆绿色吉普车,车斗里堆着白面袋子,还有几匹花布,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。
小阳正在场院里追鸡玩,听见动静就往娘身后躲。
"小阳,来,跟大伯去看大汽车。"
大伯娘蹲下身,往他兜里塞了一把大白兔。
那糖纸金闪闪的,小阳看得眼睛都直了。
娘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推了推,可指尖却在发抖。
我站在晒谷场上,看着吉普车扬起一路尘土。
娘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,衣裳让风吹得紧贴在身上,活像根枯死的树桩。
几只麻雀落在她脚边啄食谷粒,她也不赶,就那么直愣愣地望着大路尽头。
天快黑时,我过去拉她的手,冰凉冰凉的。
腊月里,小阳穿着新崭崭的海军衫回来了。
那蓝白条纹在灰扑扑的村子里格外扎眼,惹得一群孩子跟在后头看。
他给我带了本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书页散发着油墨香。
夜里我俩挤在一个被窝,他忽然凑过来问:"二姐,为啥娘看见我总抹眼泪?"
我没吭声,摸到他手腕上那个银镯子。
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,正好照在"长命百岁"四个字上,明晃晃的刺眼。
外头的老北风呜呜地吹,把房檐下的冰溜子刮得"叮当"响。
小阳翻了个身,镯子磕在炕沿上,发出清脆的一声"当——",在静夜里格外响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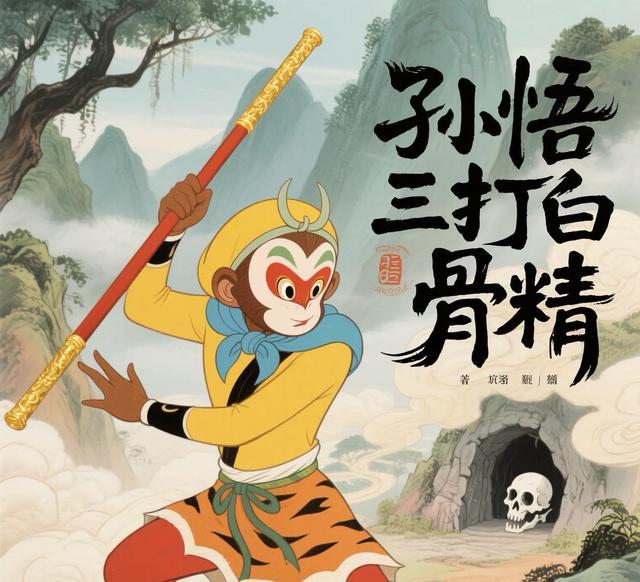
第三章:生死离别
九二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
刚进腊月,河面就冻得结结实实,冰层底下偶尔传来"咔咔"的响声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挠冰。
爹躺在堂屋的板床上,喘气的声音越来越轻,最后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,就再也没动静了。
小阳是连夜赶回来的。
他身上还穿着白大褂,胸牌在孝布底下若隐若现,上面"县医院"三个红字格外扎眼。
村里的婆子们凑在院墙根下嚼舌根:"瞧瞧,过继出去的反倒比亲生的还孝顺。"
她们说话时嘴里呵出的白气,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团雾。
守灵那晚特别冷。
娘从陪嫁的樟木箱最底下掏出个蓝布包,一层层揭开,里头是双千层底布鞋。
煤油灯的光摇摇晃晃,照得鞋底上的针脚密密匝匝的。
娘的手在鞋面上摩挲着,指甲缝里还留着纳鞋底时勒出的青印子。
"试试合脚不?"娘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
小阳二话不说,蹲下身就解皮鞋带。
他的手指头冻得发红,解了半天才解开。
新布鞋套在脚上有些紧,他站起来走了两步,香灰被踩得扑簌簌飞起来,在灵前打着旋儿。
"比牛皮鞋舒坦。"
他说着,还特意跺了跺脚。
火盆里突然爆出个火星子,正好照亮他的脚脖子。
我看见新鞋帮子在他脚背上磨出一道红痕。
娘突然背过身去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供桌上的长明灯忽闪了一下,把爹的遗照照得明晃晃的,照片里的爹好像在看着我们笑。
屋外的老榆树被风吹得吱呀作响,一片枯叶打着旋儿从门缝里钻进来,正好落在爹的灵前。
小阳跪下去捡那片叶子时,我听见他轻轻"嘶"了一声——肯定是新鞋磨得脚疼。
但他跪得笔直,就像爹生前教我们的那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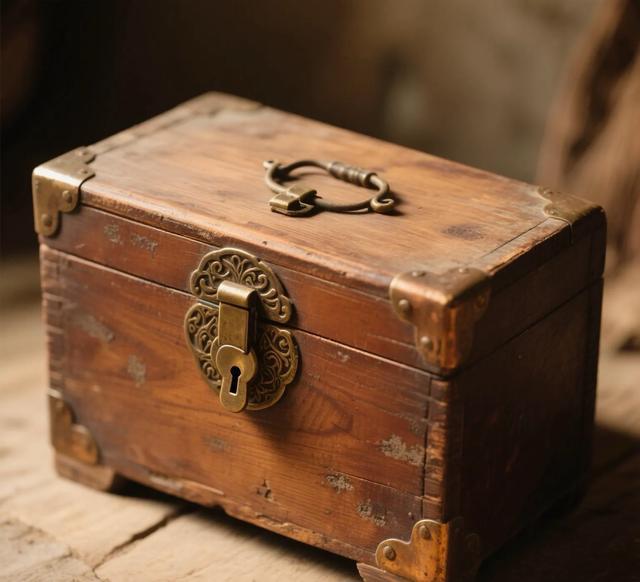
第四章:最后的团圆
娘查出胃癌那年,正是槐花飘香的时节。
小阳穿着白大褂站在县医院走廊里,手里捏着那张CT片子,对着窗户翻来覆去地看。
阳光透过片子照在他脸上,把那些阴影映得清清楚楚。
他手里的钢笔"咔吧"一声断了。
"没事,就是普通胃炎。"
小阳转过脸来对娘笑,嘴角往上扯着,可眼睛里的光却一点点暗下去。
娘坐在长椅上,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,像个等着老师发作业本的小学生。
她身上那件藏青色褂子洗得发白,领子上的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,一看就是自己缝的。
病房里的日子像凝固了一样。
娘一天比一天瘦,颧骨高高地凸出来,眼睛显得特别大。
小阳每天查完房就往娘这儿跑,白大褂口袋里总揣着些稀罕吃食——有时是几块桃酥,有时是罐头里的荔枝。
娘总说"留着给孩子们吃",可拗不过他,只好小口小口地抿。
最后一晚特别安静。
窗外的知了不知什么时候不叫了,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在地上画出一道银线。
娘突然清醒过来,眼睛亮得吓人。
她颤巍巍地伸手摸小阳白大褂上的扣子,塑料扣子被摸得发亮。
"娘对不住......"她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。
"我在城里住楼房,顿顿有肉,您还有啥不放心的?"
小阳飞快地截住话头,声音却哽住了。
他低头给娘掖被角,我看见一滴水珠砸在娘的手背上,又被他悄悄擦掉了。
葬礼那天,小阳从怀里掏出个存折塞给执事。
"按最好的办。"
他说这话时,眼睛盯着灵堂上娘的遗像。
照片里的娘还年轻,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,笑得腼腆。
执事翻开存折看了看,倒吸一口凉气——那数目够买两头大牯牛了。
烧纸钱的铜盆里,火苗蹿得老高。
小阳跪在那儿,一张一张地往里添纸钱。
火光照得他半边脸发亮,半边脸藏在阴影里。

尾声:岁月的答案
大伯和大伯娘搬来那天,正是开春时节。
院里的老梨树冒出了新芽,白生生的。
大伯的行李不多,就两个樟木箱子,漆皮都剥落了,露出里头发红的木头。
小阳的女儿丫丫跑前跑后,手里攥着一把刚摘的野花,黄的蒲公英,紫的地丁,还有几枝叫不上名的小蓝花。
"这是奶奶,那是姥姥。"
丫丫踮着脚往供桌上摆花,小手胖乎乎的,动作却认真得很。
供桌上并排放着两个相框,一个里头是娘年轻时的模样,梳着两条乌油油的大辫子;另一个是大伯娘四十岁生日照,穿着件蓝底白花的的确良衬衫。
两束野花挨在一起,风从门缝钻进来,花瓣就跟着轻轻颤。
清明那天下着毛毛雨,细得像筛出来的面粉。
弟媳领着丫丫在院子里收拾上坟的东西,新蒸的白面馒头,炸得金黄的麻叶,还有一瓶老白干。
"慢点跑,"弟媳拽住丫丫的衣角,"别摔着姑妈。"
丫丫咯咯笑着往我这边扑,辫梢上系的红头绳一跳一跳的,像两只红蜻蜓。
我站在屋檐下躲雨,看着雨水顺着瓦沟往下淌,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
三十年前那个雪天突然就浮在眼前——大伯的军大衣,娘站在雪地里单薄的身影,小阳兜里的大白兔糖纸沙沙的响。
那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,谁知道日子就像这屋檐水,滴着滴着,竟滴成了一个圆。
丫丫跑过来往我手里塞了朵野花,花瓣上还沾着雨水。
"姑妈,给你。"她仰着脸笑,嘴角两个小酒窝,跟小阳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我弯腰把她抱起来,她身上有股子阳光晒过的棉花味道,暖烘烘的。

原来有些路,走着走着,就团圆了。
全文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