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月1000元,年轻人开始花钱租“老板和同事”
花钱制造 " 在职 " 假象
早晨八点,北京东五环某小区,晓航起床洗漱,坐下来吃母亲准备好的早餐。
" 最近工作忙吗?" 面对父亲的例行询问,他含糊地应了一声,快步走出家门。
九点一刻,他到达国贸某写字楼,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,和 " 同事们 " 说早安。" 老板 " 笑眯眯地看着他,对于他的迟到并不在意。
坐到自己的工位上,晓航从双肩包里拿出电脑开始上网,上招聘网站发简历。
十一点半,有 " 同事 " 过来叫他吃饭,他没去,拿出母亲为他准备好的爱心便当到茶水间的微波炉加热。
中午吃完饭,他靠在椅子上一觉睡到两点多。醒了之后打开电脑继续 " 工作 " ——发简历、打游戏,和朋友在微信上闲聊。
这期间," 老板 " 过来巡视过几回,给 " 摸鱼 " 的晓航送来一个苹果和一杯酸奶。
差一刻五点,晓航把电脑塞进书包,抢先走进还没有迎来下班高峰的电梯。
经过 " 老板 " 的办公室,老板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,不但没有责怪他早退,还温柔地跟他说 " 明天见 "。
地铁上,晓航收到母亲的微信:" 晚上吃火锅,今天加班吗?"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良久,他回复:" 不加。"
这是晓航在国贸 " 上班 " 的第六个月,朝九晚五,周末双休,工资为 0。不仅没有工资,他每个月还要给老板 " 倒贴 "1000 多元。

图 | 晓航 " 上班 " 的北京国贸 CBD
社交媒体上,有人把晓航这样的行为称作 " 假装上班 ",而他 " 假装上班 " 的地方则被叫做 " 假装上班公司 "。
去年年底以来," 假装上班公司 " 在社交平台大火。企查查显示,2025 年,全国已有多家以 " 假装上班 " 为名注册的新公司。
Queenie 是北京望京地区一家传媒公司的创始人。
2025 年 4 月初的某一天,她突发奇想,在小红书上发表了一篇 " 望京假装上班事业部 " 成立的笔记,没想到很快就爆了,当天就有三四十人私信咨询,就连远在新西兰的朋友也看到了。
" 我很少发笔记的,这篇笔记能爆其实很意外。"
在招募帖里 Queenie 写道:" 你是否怕失业的自己被亲友看穿?是否觉得自由职业在家效率低下,工作需要督促?或者搞副业又担心没空间?又或者被家务带娃逼得想‘静一静’?都可以,这里就是你的新‘ office ’ !"

图 | Queenie 的办公室
Queenie 的办公室位于望京核心区域,总面积 130 平方米,平时主要接一些商业广告项目。这几年业务量下滑,员工减少,办公室越来越空。有一些从大厂出来准备创业的小伙伴主动找到她,要求租用多余的场所,用于开会或者讨论创业项目。

图 | Queenie 的办公室
Queenie 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,一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承载着她多年的创业记忆,她不想换地方。朋友的想法给了她启发,她索性借助 " 假装上班 " 这个网络热梗对外营业。
按市场价,她把普通工位定为日租 50 元,因为刚开始 " 试水 ",体验价为每天 29.9 元。除了出租工位,还有一些增值服务,比如简历优化、周末社群、线下沙龙等等。

图 | Queenie 的办公室
" 我自己也经历过需要找地方办公的阶段,那个时候主要是去星巴克,但是星巴克人多嘈杂,并不适合办公。提出‘假装上班’这个说法,并不是我有意在炒概念,主要还是基于市场现状,一些失业的人或者自由职业者,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。"
从出租房间到出租 " 人生剧本 "
上海虹口,小盛也开了一间 " 假装上班公司 ",日租 30 元,整租 600 元包月,工位随便使用,水电网及公共空间全部免费。
不仅如此,公司还提供情绪价值的输出," 老板 " 会假装分配工作给 " 员工 ",而 " 员工 " 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,并把方案甩到办公桌上直接怼老板。
消息一出,有几千人响应,小盛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也炸了锅。
与 Queenie 单纯出租个人办公室的模式不同,小盛经营的 " 假装上班公司 " 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概念包装的共享办公空间。


图 | 小盛的共享办公空间
这种情况在业内相当普遍——许多运营商通过 " 假装上班 " 这个时髦噱头吸引客户,但其商业本质仍是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办公空间租赁业务。
" 传统共享办公空间主要服务于企业客户,以初创公司和团队为主。现在为拓展市场,运营商开始向个人用户开放租赁服务。"
陈晓记得,以前她在共享办公室上班时,一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区域被压缩成了几十个大小小的办公场所,狭小的格子间里坐满了各种各样热血沸腾的创业者。
" 随便在走廊或者会议室转一圈,听到的都是融资的话题,会议室的黑板上没来得及擦掉的内容也是和融资有关的。当然,创业公司也大都很短命,走了一茬又一茬。"
陈晓所在的共享办公室是一个可容纳四五个人办公的独立空间,月租不到 3000 元,而就在他们对面的一幢楼里,租一间同样的办公室则需要几万元。
"CBD 这样的地方寸土寸金,如果没有资方,初创企业真是负担不起。"

图 | 晓航 " 上班 " 的北京国贸 CBD
2010 年,陈晓大学毕业,第一份工作是在创业公司做策划。这一年,共享办公模式首次被引入中国,最初仅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创业园区零星出现。
2015-2016 年,共享办公迎来爆发式增长,优客工场、WeWork 中国等品牌迅速扩张。巅峰时期,优客工场估值突破 30 亿美元,WeWork 中国估值更达到 470 亿美元。
然而好景不长,2018 年后行业开始下行。2020 年市场规模从 2019 年的 103 亿元骤降至不足 200 亿元。
2021 年,纳什空间、FUNWORK 等知名品牌相继关停,15 家主要运营商中超过三分之一退出市场。到 2025 年,曾经辉煌的优客工场市值仅剩 166 万美元,WeWork 全球市值更是从峰值暴跌至 4500 万美元。
目前行业整体规模较巅峰期萎缩超 60%,运营项目数量从最高时的上千个缩减至不足 300 个。
经历过从狂热到理性的转变,如今,幸存企业多转向轻资产运营,试图通过服务创新寻找出路。
雨后春笋般出现的 " 假装上班公司 ",可以说是共享办公的另一种生存之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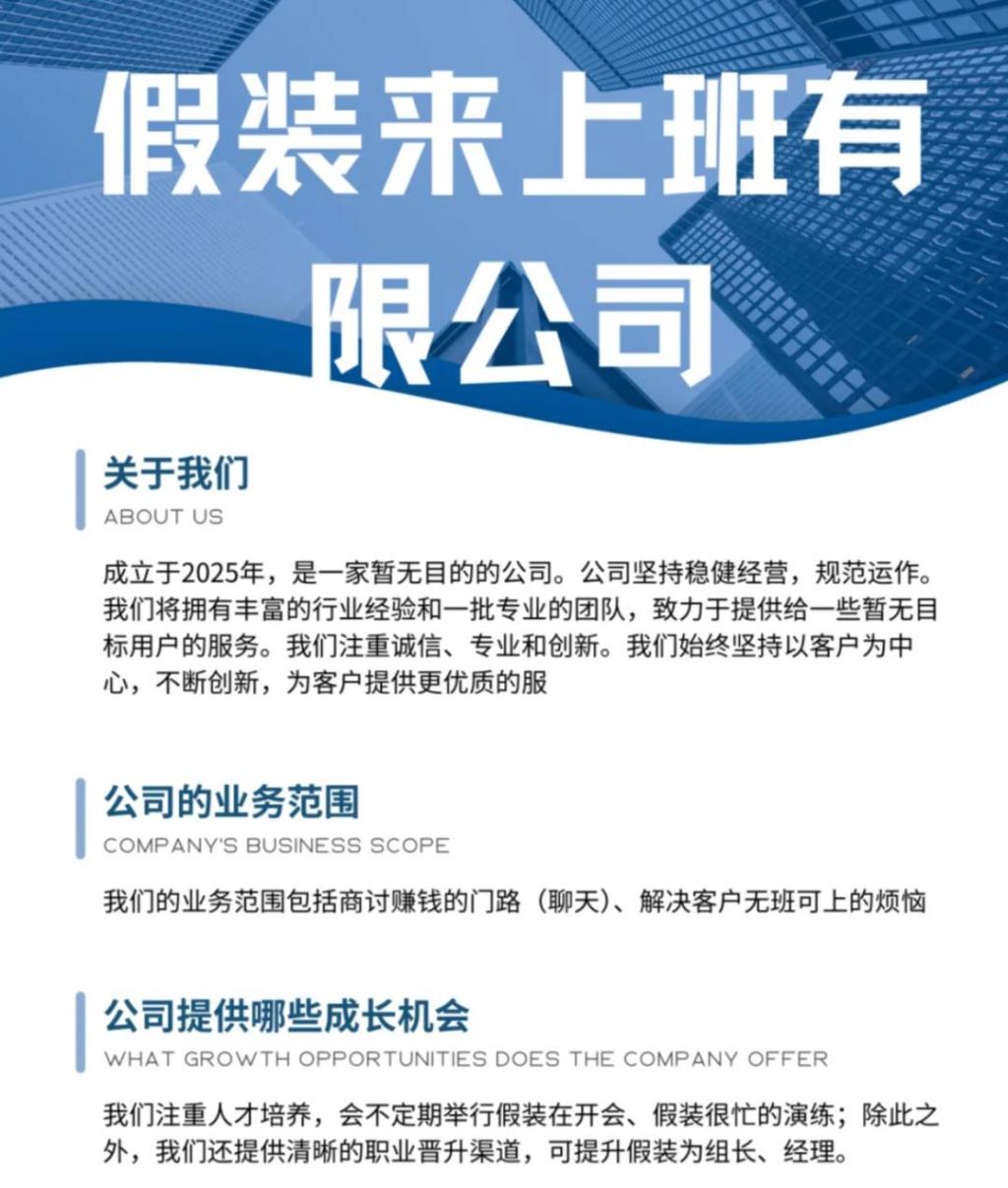
前年,陈晓自己也成了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,虽然她没有租用共享办公室,但在她看来,共享办公空间为创业公司提供了理想的运营选择。
这种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,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商业生态,让创业者能够在跨行业的交流中获得成长机会。
" 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,‘假装上班’本质上是为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种过渡方案。对失业者来说,它延续了工作状态;对需要集体办公的创业者,它提供了工作空间和心理支持;对高压职场人,它创造了一个可以短暂逃离的喘息空间。"Queenie 解释说。
" 职场演员 " 的生存逻辑
" 假装上班 " 这一概念,最早出现于去年的热播综艺《非常敢想队》。当 Queenie 考虑将空置的望京办公室对外出租时,节目里李川等人演绎的喜剧情节立即浮现在她的脑海中。
" 付费上班 " 的行为看似荒诞,却折射出当代职场人面临的多重困境:被动失业的生存焦虑、传统家庭对 " 稳定工作 " 的执念,以及职场文化中 " 以工定值 " 的隐性规则等。
晓航成为其中一员绝非偶然。从小到大,他都是亲朋口中 " 别人家的孩子 " ——小镇做题家、985 硕士毕业、外企年薪 30 多万的小白领。
变化源于半年前的一封裁员邮件,因业务调整,晓航所在部门全员被 " 优化 "。
连续投了很多简历石沉大海后,他开始在国贸的共享办公空间 " 上班 ",用每月 1000 多元的支出维系着 " 在职 " 的假象。

" 主要是不想让父母失望。" 晓航说,他一直记得拿到外企 offer 那天母亲开心的表情。在老家亲戚的眼里,这个考上名校、留京工作,并且把父母接过来的孩子,是全村人教育子女的榜样。
" 儿子出息了,妈妈为你骄傲!" 母亲的这条微信,成了晓航每天坚持 " 上班 " 的精神支柱,推动着他继续这场维持体面的 " 职场表演 "。
除了晓航这样的年轻人,一些已婚、上有老下有小,被动失业却不愿家人知道的中年人,也是 " 假装上班公司 " 的 " 客户 "。
对他们而言,这个虚拟职场不仅是对外维持体面的 " 社会面具 ",更是对抗生活失序感的精神堡垒。
" 假装上班 " 反映了当代职场人面临的身份焦虑与社会压力。当 " 你在哪里工作 " 成为社交开场白," 事业有成 " 仍是主流价值标杆," 假装上班 " 就成了一种无奈的生存智慧。
而 " 假装上班公司 " 则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传统职场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裂缝,为都市人提供了应对现实压力的缓冲地带。

除了失业群体,自由职业者也是 " 假装上班公司 " 的主力用户。调查显示,超 60% 的参与者表示,就想听人问一句:" 你想喝奶茶吗?"
针对这一部分群体,上海某共享办公空间推出 " 虚拟团队 " 服务,用户可付费加入" 市场部 "、" 技术组 ",参与模拟会议、茶水间闲聊,甚至组团点外卖。
心理学家分析,人类天生具有群体归属需求,而远程工作者长期独处容易产生孤独感," 租同事 " 其实是花钱购买社交慰藉。
没有真同事,但需要真社交,对于这部分人而言," 假装上班 " 是他们的 " 社交刚需 "。
杨洋是一位自由撰稿人,她表示:" 虽然写稿时不需要交流,但有人陪着一起工作,一起吃午饭,工作会更有劲头。"
" 假装上班不只是为了应付家人。有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环境就会失去状态,他们需要特定的空间来营造上班氛围,这样才能保持工作效率。"
杨洋举例说,她的一位朋友一旦失去工作环境就会陷入焦虑,但只要回到办公室,就能立即恢复工作状态。
对他而言," 上班 " 这个动作已经成为启动工作模式的必要开关。
结尾
在这个快节奏且充满压力的时代," 假装上班公司 " 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人们在职场和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挣扎。
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办公场景的场所,更像是一处心灵的避风港,让那些在现实浪潮中漂泊的灵魂能找到短暂的慰藉。
然而,这看似新奇的 " 假装上班 " 模式,终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对策略。
我们不能永远躲在这个精心构建的 " 虚拟职场 " 里,用表演来逃避真实的生活。
当人们从这里重新获得力量,勇敢地迈出步伐,去直面失业、孤独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时,或许才是真正理解了 " 假装上班 " 背后的意义。
希望有一天,社会能给予每个人更包容的环境,让工作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,让人们无需通过 " 假装 " 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
到那时," 假装上班公司 " 也许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但它所承载的特殊记忆,以及曾给予无数人的温暖,将永远被铭记,成为时代发展进程中一段独特的注脚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本文均采用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