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哥一年往家里跑8趟,母亲去世后,他却不让兄弟姐妹再回家
二哥站在院门前,手里捏着那封泛黄的信,目光如同一潭死水。"娘走了,你们别再回来了。"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我叫王继平,家在河北一个偏僻小村。我们兄妹四人,排行老四,上面有大姐继芳、二哥继业和三妹继红。
二哥自打娘还在世时,一年要从城里回家八趟,风雨无阻。每次回来,他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,有时候是城里的点心糕点,有时候是娘常用的红花油和跌打损伤药。
娘每次看到二哥回来,那双浑浊的眼睛就亮得像星星。"业子回来啦!"她的声音会比平时高八度,整个人也仿佛年轻了十岁。
那时候,我们都笑话二哥是"妈宝男",他也不恼,只是摸摸鼻子,憨厚地笑。二哥生来就是这副老实巴交的样子,说话慢条斯理,做事一丝不苟。
"笑啥笑,"大姐常数落我们,"人家二哥懂得孝顺,你们懂个啥?"大姐嘴上这么说,可每次她从县城回来,也不过是空着手来,满载而归。
1989年的春天,青黄不接的日子。那年麦子长势不好,村里人天天望着天发愁。二哥背着个大行李包,从城里回来了。
那是他第八次回家,我清楚记得,因为娘那天格外反常。她神秘地把二哥叫到西屋,吱呀一声关上了那扇漆掉得斑驳的木门,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话。
院子里的老榆树下,我和三妹正忙着摘菜。"你说娘跟二哥嘀咕啥呢?"三妹一边择着豆角一边问。
"谁知道呢,"我无所谓地耸耸肩,"可能又在埋怨大姐不常回来吧。"
半晌,西屋的门开了。二哥出来,眼眶红红的,手里攥着一封信。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,他只摇摇头,说是娘让他帮忙办点事。

那个春天,院子里的白杨树抽出新芽,老屋檐下的燕子又回来筑巢。二哥在家待了三天,临走时,我发现他偷偷量了老屋的砖墙和门窗。
"量这干啥?"我好奇地问。
"没事,随便看看。"他含糊其辞,把卷尺塞进裤兜。
那年秋天,院子里的柿子熟了,红彤彤地挂在树上,像一盏盏小灯笼。娘的咳嗽越来越严重,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。我从镇上的卫生院买了药,可不见好转。
"城里医院大,设备好,"大姐说,"咱们带娘去县城看看吧。"
二哥闻讯,立马从城里赶了回来。他瘦了,脸上的胡茬密密麻麻,手上多了几道老茧。"上我单位的医院,"他说,"费用我来出。"
那时候住院难,没有关系住不进好病房。二哥不知用了什么法子,给娘安排了个单人间。他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,喂水喂药,端屎端尿。
深夜,走廊的白炽灯光冷冰冰的。我去病房送换洗衣服,看到二哥坐在床边,握着娘的手,正轻声说着什么。娘虚弱地点头,眼角有泪光闪动。
"继平来了,"娘看到我,招招手,"你二哥这孩子,又不听我的。"
"咋了?"我问。
"没啥,"二哥打断了娘的话,"娘想吃家乡的咸菜了,我说明儿让你送点来。"
住了半个月院,娘的病情好转了些。二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单位和医院之间,眼睛里都是血丝。他单位正赶上重要项目,领导催得紧,可他硬是请了假。
"不差这几天,"他说,"咱娘要紧。"
那年冬天特别冷,北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田野。村口的大槐树被风折断了一截粗枝,砸坏了老刘家的院墙。

娘走了,走得很安详,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她走的那天,窗外下着小雪,雪花轻轻落在屋檐上,像无声的叹息。
办完丧事,二哥忽然变了个人似的,告诉我们:"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,以后不用再回来了,老家的事我来处理。"
大姐当时就不干了:"娘的坟还没出三年呢,你凭啥不让我们回来?"
"回来干啥?添乱吗?"二哥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我们说过话,我们都愣住了。
"这房子是咱爹娘留下的,你说不让回就不让回?"大姐提高了嗓门。
二哥紧抿着嘴唇,眼神闪烁:"我是老二,按理说没权力做主。但娘临终前跟我说了,这老宅以后归我了。"
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房产归属的字样,娘的手印盖在最下面,像一片落叶。
"娘糊涂了吧?"三妹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张纸,"怎么能把祖宅给你一个人?"
"是真的,"村支书老张帮腔道,"你娘生前找我做见证的,这事我知道。"
那天,我们不欢而散。大姐拂袖而去,三妹哭着跟上,只留下我站在原地,看着二哥瘦削的背影。
"真不用我们回来了?"我问。
二哥背对着我,肩膀微微颤抖:"各人有各人的活法,继平,你的日子还长着呢。"
那时候,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。大姐夫刚从纺织厂下岗,靠摆个小摊卖袜子维持生计。三妹的孩子上初中,正是用钱的时候,她和姐夫在镇上的服装厂做工,每天起早贪黑。
我呢,刚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,月供压得喘不过气。每月发了工资,交了房贷,剩下的钱只够勉强度日。
只有二哥,在城里的机械厂上班,工作还算稳定。但他从不提自己的情况,每次问起,他都摆摆手说:"凑合过呗,跟你们一样。"

连着两个春节,我们都没回老家。大姐几次提起想回去看看,但一想到二哥那冷淡的态度,又打消了念头。
"亏我以前还觉得他孝顺,"大姐常在电话里抱怨,"现在看来,不过是为了霸占老宅。"
三妹也附和:"二哥变了,娘刚走那会儿,他就变了。"
只有我,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二哥那样的人,怎么会为了一所破旧的老宅翻脸不认兄妹?
第三年春节,大姐实在忍不住了,硬是拖着全家回了村。她想去拜祭娘,也想看看老宅现在什么样了。
她刚到村口,就听到邻居老刘家的媳妇在井边洗衣服,嘴里念叨:"王继业真是个好儿子,这些年把老宅收拾得多好啊,就是太辛苦了,听说晚上还在电灯下做木工活..."
大姐心里一惊,二话不说直奔老家。刚进村口,她就愣住了。记忆中破旧不堪的老宅,现在门楣焕然一新,院墙刷得雪白,大门口的石狮子也擦得锃亮。
"继业!"大姐站在院子中间大喊。
二哥从屋里出来,穿着件灰布棉袄,腰间系着个木工用的工具袋。看到大姐一家,他愣了愣,随即笑了:"来了啊,刚好,饭马上就好。"
那天,二哥做了一大桌子菜。有娘生前最爱做的红烧肉,有地窖里自己腌的咸菜,还有刚从集市上买来的鲜鱼。他忙里忙外,脸上挂着笑,眼睛却是红的。
团圆饭上,大姐端着酒杯,直视二哥:"继业,实话实说,这些年到底怎么回事?"
二哥眼神闪烁,放下筷子,喉结滚动了几下。窗外的腊梅在寒风中摇曳,屋内炉火正旺,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。

空气凝固了一般,连三妹的孩子都安静下来,不再吵闹。
"去地窖看看吧。"二哥终于开口。
地窖在后院的角落,从我记事起就在那儿。小时候,我们常躲在里面捉迷藏。娘把腌菜、土豆和白萝卜都存在那里,冬天取出来,格外清脆爽口。
二哥拿着手电筒在前面引路,我们跟在后面,屏息凝神。地窖里弥漫着泥土和陈年咸菜的气息,墙上挂着几串干辣椒,在灯光下投下诡异的影子。
在最里面的角落,我们发现了一个老木箱。那是爹生前做的,上面雕着简单的花纹,锁早已锈迹斑斑。
二哥从脖子上取下一把小钥匙,打开了箱子。箱子里全是娘的遗物:一件织到一半的毛衣,那是她准备送给二哥的孩子的,可惜没等织完人就走了;几张泛黄的全家福,那是我们小时候照的,爹还在世的时候;还有一本记事本,娘不识几个字,却坚持记日记,记录家里的大事小情。
大姐翻开记事本,泪水立刻涌了出来。记事本上,娘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:"继业说要给我修老屋,我哪舍得孩子们花钱,可我真想有个像样的家,让孩子们回来,过年时热热闹闹的..."
大姐翻到最后一页,发现了那封信的复印件。原来,娘生前最大的心愿,就是把老宅修缮一新,让分散各地的子女有个回家的地方。她怕给子女添负担,只托付给了二哥一个人。
信中还提到,娘希望老宅能保留原来的样子,只是加固翻新,不要大拆大建。"这是你爹的心血,"娘写道,"我走了以后,你们兄妹还有个根在这儿。"
"为啥不告诉我们?"三妹问,眼泪啪嗒啪嗒地掉。
二哥搓着粗糙的手,低声道:"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。我那破单位也快不行了,每月就那点死工资。我想着...与其让大家跟着操心,不如我自己慢慢来。"

他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:"我怕你们知道了,非得出钱不可。大姐夫刚下岗,三妹孩子上学,老四又刚买房,哪有闲钱?我就想,娘这心愿,我一个人扛着就行了。"
原来这些年,二哥把单位发的福利全攒下来,换了钱。下班后还接些木工活儿,给人修家具、做木匠活,一点一点攒钱修缮老屋。他手上的茧子,脸上的皱纹,都是这么来的。
"可你为啥不让我们回来?"大姐问。
二哥叹了口气:"我怕你们看到老宅修了一半的样子,非得帮忙不可。那时候老屋后墙快塌了,我刚找人垒好砖,还没来得及粉刷。你们要是看见,指不定要心疼成啥样,非得伸手不可。"
他抬头看着我们,眼神诚恳:"再说了,你们回来不得添些开销?城里人回乡下,邻里间不得走动走动?我那点工资,能省则省吧。"
想起二哥常年不买新衣服,冬天穿着磨破的棉袄,我心里一阵酸楚。当年我买房,他二话不说借给我两千块,说是单位发的奖金。现在想来,那哪是什么奖金,分明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。
我走出地窖,仔细打量这个我长大的院子。砖瓦错落有致,檐角雕花精细,院墙上爬满了冬青。想起小时候漏雨的房顶,坑洼的院子,不由得鼻子一酸。
房梁是新换的,做工精细;地面用青砖铺就,窗户换成了防盗的铝合金,但整体的格局和原来一模一样。前屋三间,东西厢房各两间,后院还是娘种菜的园子,一草一木都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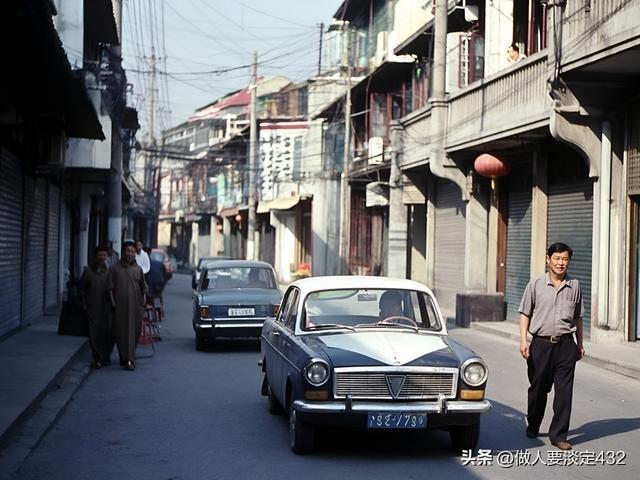
"你这个傻子!"大姐拍着二哥的肩膀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"我也没啥大本事,就这点手艺。"二哥憨厚地笑着,眼角的皱纹像秋天的树叶,"娘生前最怕给我们添麻烦,我就想着,至少得把这个家..."
他哽咽了,没再说下去。
三妹眼圈红红的,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,那是娘六十大寿时照的。照片里,娘笑得眯起了眼睛,我们几个站在她身边,青春靓丽。转眼间物是人非,只剩下照片里的笑容定格在那一刻。
"还记得咱娘过六十大寿时,"三妹抹着眼泪说,"她最大的愿望是啥?"
"希望子女们常回家看看。"我说。
"是啊,"二哥点点头,"她就这么个愿望,也不嫌简单。"
那天晚上,我们一起翻看了娘的相册。有一张是全家人围坐在老屋前的合影,娘坐在中间,笑得那么满足。照片背面,有娘的笔迹:"家和万事兴"。
相册的最后一页,夹着一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:"继业,别告诉他们我的病,让他们安心过自己的日子。娘这辈子没啥不满足的,就希望你们都好。"
看到这里,大姐再也控制不住情绪,抱着二哥放声大哭:"你这个傻子,啥都自己扛着,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!"
二哥拍着大姐的后背,笑着说:"大姐,你哭啥?咱娘看见了,该说我没出息了。"
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娘站在门口,笑着看我们闹。她总说,儿女在一起,就是她最大的幸福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们去集市买了一棵桂花树苗。娘生前最爱桂花的香气,总说闻着这味道,心里就踏实。
二哥挖坑时,铁锹碰到了什么硬物。扒开泥土,竟是一个小铁盒。盒子里是娘攒的养老钱,一共三百八十六块,还有张字条:"留着给继业添置工具"。

"你看咱娘,"二哥哽咽着说,"一辈子想着别人,从来不为自己。"
三妹蹲下身,抚摸着那个小铁盒:"二哥,对不起,这些年我们误会你了。"
"有啥对不起的,"二哥摆摆手,"咱们是亲兄妹,血脉相连的。娘在九泉之下看到咱们和和睦睦的,该多高兴。"
我们把桂花树栽在院子正中,那是娘生前最喜欢的花。初春的风拂过树梢,似乎带着娘的气息。树下,我们放了一块小石碑,上面刻着娘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
"以后,咱们每年都回来。"大姐说。
"对,"三妹附和,"过年过节的,全家人一起,就像小时候那样。"
二哥站在一旁,手里攥着那把已经用旧的木工锤。阳光下,他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,但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明亮。
那天下午,邻居们都来了,围着看我们栽的桂花树。老刘家的媳妇带了自家腌的咸菜,村支书老张提了壶自酿的米酒,连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王婶也送来了自家磨的豆腐。
"你二哥这些年干的好事,全村人都看在眼里,"老张端着酒碗对我说,"去年村里修路,他一个人捐了五百块。前年李家老太太生病,他半夜骑自行车送去县医院。就这么个好人,你们兄妹可得好好待他。"
听着乡亲们的话,想起这些年对二哥的误解,我心里又是愧疚又是感动。
二哥摸着老茧的手,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粗糙。他望着远处,眼神柔软:"娘常说,家是树的根,人再远也得记得回来看看。我这辈子没啥大志向,就想把这个家守好,等你们想家了,随时能回来。"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,分给我们每人一把:"老宅的钥匙,我配了新的。以后,这里就是咱们共同的家。"
大姐接过钥匙,紧紧握在手心:"继业,这些年苦了你了。"
"苦啥呀,"二哥憨笑着,"我一个光棍汉,守着老宅,种种菜,养养鸡,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"
他没说的是,单位里的女会计早看上他了,几次暗示想嫁给他,他都避而不谈。乡亲们都说,王继业年纪不小了,该成家了。他总是笑笑说,等把家里的事情都料理好了再说。
如今看来,他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家,献给了对娘的承诺。
天色渐晚,村子笼罩在暮色中。远处传来牛铃声和孩子们的笑闹声,炊烟袅袅升起,弥漫在乡村的上空。
二哥站在院子中央,指着远处的农田说:"明年我打算在后山那块地种些果树,到时候结了果,你们带着孩子来摘。"
我抬头看那棵小小的桂花树,突然明白:家不是一个地方,而是一种牵挂。二哥用他的方式,为我们守住了这份牵挂。
我想起小时候,二哥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们;上学时,他总是把新课本让给我,自己用旧的;工作后,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了娘买了一台缝纫机。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把最好的都给了别人,自己默默承受着一切。
夕阳西下,我们肩并肩站在院子里,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。二哥的肩膀略微佝偻,却依然坚实可靠。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,无论风雨多大,始终守护着这个家。
我想起娘生前常说的一句话:"人这辈子,不在乎活得多久,而在乎活得有没有意义。"二哥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,但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孝与爱。

桂花树下,我们约定,无论以后走多远,都要记得回家看看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。